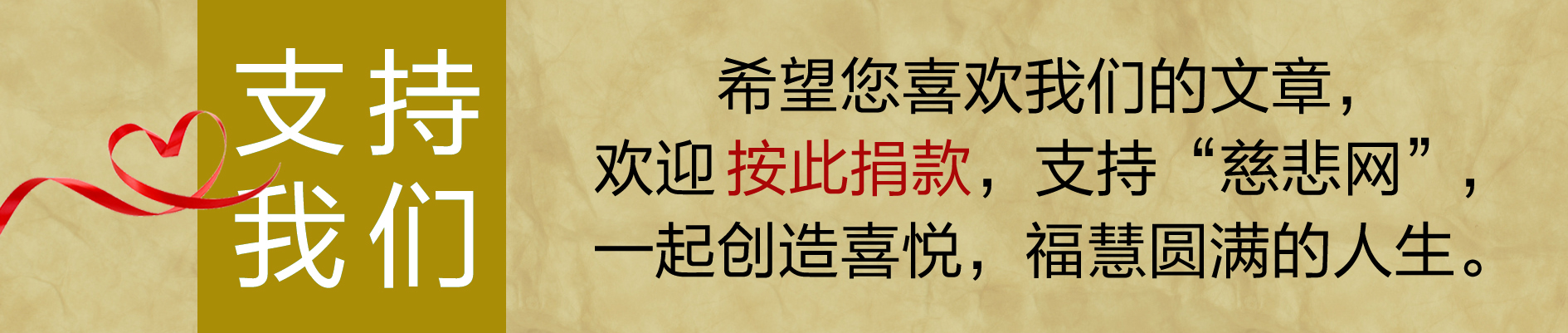【 初 心 不 变 】
《2019祝福文化尼泊尔行番外篇——旅人碎语》
一串金刚菩提一如来
灭教、逃亡、迁徙、传承……,于是释迦族经历着以千百年计的苦难与磨练。
“业力”从不应成为“恶”的藉口。善恶虽无绝对,难以非黑即白,但我始终坚信,任何的伤害,都应被谴责。似是而非地解读业力,只会姑息养奸。
在大是大非面前,这是我坚守的原则,不能逾越的界线。
文·叶伟章 摄影·徐莉嘉
~

亲爱的S’s,我想念你,我在一万零三百六十三公尺的高空上,想念着在地面上的你。临行前一天,我们匆匆见了一面,下车时,你说,旅程愉快。嗯,我轻声应着,一切如此轻盈,和平日的告别并无二样,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其实只是八天的行程——然而我竟在二十四小时后开始想念你。
我习惯在出远门时带上一本书。总以为候机时,夜里在酒店时,会需要那么一本书来打发时间,但往往我老顾着说话,最后其实也没翻上几页。
这趟带的,是德国作家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多年后重读,竟如初阅,字字句句都觉陌生,想来许是当初读的译本不同,又或二十多年后少年已长成大叔,心境与感悟都有别于从前。
会带这本书出门,自不是偶然随手,说起来其实还挺矫情刻意的,因着这趟行程是前往佛陀的出生地——尼泊尔。
祝福文化每年都会组三两团到受助地区,实地了解当地情况。
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块长条
亲爱的S’s,你知道我和尼泊尔一直有着渊源,或者说,因着移工的到来,让我对这国度产生了情感。
那时我在感情路上触礁,于是每天都独自一人坐在公园里。忧伤时,我总习惯独处,伴陪着我的,是附近住宅养的一只土狗。公园的另一隅,几位尼泊尔移工在喝酒,微醺时或唱歌或笑闹;而我,始终安静地坐在属于我的角落。终于有那么一次,其中一位向我走来,他披着一头卷曲长发,赤着膊挺着圆大的肚皮,“一起喝酒吧。”他说。
于是我们成了朋友。后来在公园里我不再一个人,也渐渐不再忧伤。我们几乎每晚下班后,都一起喝酒,他知我喝不惯印度进口的啤酒,发薪时就会买好我平日喝的白啤。我学着尼泊尔语的“你好”、“谢谢”、“吃饱了吗”、“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学会了他们惯常玩着的扑克游戏“吉蒂”;他常邀我到他家吃他们做的咖哩山猪肉;也试过喝醉了就一起卧在睡得东倒西歪的人堆里……
当然不止这些,还有更荒唐的。我陪着他跟踪印尼籍女友,追查她与他同乡幽会;试过把他那老爱向我劝酒的室友灌醉,结结实实地吐了满房间;我曾带他和友人到佛寺,我忙着烧香他们忙着拍照,我知道,于他那是难得的出游……
我们如此这般腻着,少说应该有三两年,直至他回乡。我在他上车去机场前,在他家门口微笑着给他一个结实的拥抱。“你一定要来尼泊尔。”他说。我轻轻点着头。我在他离开以后,独自一个人坐在我们初识的公园,终于没能忍住,嚎啕大哭了起来,声嘶力竭地哭,仿佛那是一场永别。
是的,永别。亲爱的S’s,我从不相信永恒,我清楚知道,情感这回事和思念一样虚无缥缈。离开,即是句号;即使再见,也是另一篇章。他初始还会给我拨电,但我们终究必须展开没有彼此的生活。后来辗转得知他在家乡开雇用车、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父亲去世……;然而,我们都未能再参与彼此的生活。
再后来,我遗失了手机,他没再上脸书,于是我们彻底断了联系。然而S’s,你记得我曾跟你说过的小王子和狐狸的故事么?狐狸不吃麦子,但因为小王子的发色,所以麦田对狐狸而言有了不同层次的意义。
于是,尼泊尔于我,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块长条。
亲爱的S’s,你知道,这几年我惯于安静的生活;大抵,如果不是因为祝福文化,我是绝不出远门的。
祝福文化,慈善团体,成立于2014年,掌舵的是前媒体人,在媒体界举足左右便有轻重的萧依钊。
她虽是媒体人,但也致力于文化与慈善事业,曾获2013年度《南方.华人慈善盛典》所颁予的慈善人物奖、第四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海外地区的“传播贡献奖”、马来西亚“杰出华裔女性巾帼——爱心大使奖”等奖项。
2014年,我们离开媒体以后,她创立了祝福文化,继续着她早前的助学工作,受助对象包括了我国原住民、尼泊尔、印度、缅甸以及中国山区的孩童。此外,也有一些贫穷家庭个案。据知,之后还会加入“临终关怀”这项目。
每年,祝福文化都会组三两团,到助学地区实地考察,今年的其中一站,正是尼泊尔。
我的工作,是照看着行程与团员,以及当一名文字记录者。
然而S’s,我忘了是否曾告诉你,这样的双重身份叫我疲累。我并不真是大家所想像的“多任务功能者”(multitasking),更多时候,我会希望自己可以置身度外,专注而沉潜地观察团里的人与事。每次出行,我都觉得自己只是个“时间管理者”(timemanager);因此,我从未满意自己的书写,从未。
但又或许,这其实是我给自己的藉口与台阶——始终未能把文章写好的堂皇与冠冕——谁又敢说不是呢?

肩负了传承佛法的重担
关于这趟尼泊尔的行程,已写在《把祝福带进佛国——尼泊尔助学团记事》特稿里,此处不赘述。想要说的,是一些被落下的零碎细节,以及无关紧要的心情。
是的,细节与心情,譬如说行程里我们穿过了释迦族的社区,去到了遐迩闻名的黄金寺。
黄金寺又称克瓦寺(Kwa Bahal),位于古城帕坦,与杜巴广场(Durbar Square)仅徒步距离。黄金寺不大,建于西元12世纪,以华丽的镀金雕饰与精致的铜雕让人印象深刻。金碧辉煌之余,雕刻的密集实属叹为观止,细致的程度堪称鬼斧神工。
然而更吸引我的,却是中庭一隅的火供仪式。但见四人围于火炉三边,居中长者身穿独特服装,右边的男人一边念诵经文,一边把谷米、茶叶等撒进火炉里,左边的那位则负责添柴枝。细问才知,是长老上任的仪轨。
导游与我们说,尼泊尔曾是印度教君主制国家,对于佛教全面打压,因此境内不见出家众。“要是被发现信仰佛教,是会被捉去坐牢的啊。”她说。于是释迦族肩负了传承佛法的重担,以在家人的身份,一代又一代传承着佛陀的智慧,以及古老的仪式。
公元九世纪以降,在伊斯兰与婆罗门教统治者的先后控制下,佛陀的故乡伽毗罗卫城的光辉历史彻底“被消失”。当时的释迦族人逃向了缅甸,以及加德满都谷地。
灭教、逃亡、迁徙、传承……,于是释迦族经历着以千百年计的苦难与磨练。乃至今日,宗教与宗教间、政治与宗教间,争战与打压从未消停。
S’s,我知道你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一切系为因缘。《大唐西域记》里牧牛人投生为恶龙,意欲覆灭整个国,是为因缘;《杂宝藏经》中的离越尊者,难逃牢狱之灾,是为因缘。因着业力推动,所有的善与恶,仿佛从来不由自主。从超然的宇宙观来看,或许世事确是如此。
然而S’s,“业力”从不应成为“恶”的藉口。善恶虽无绝对,难以非黑即白,但我始终坚信,任何的伤害,都应被谴责。似是而非地解读业力,只会姑息养奸。
在大是大非面前,这是我坚守的原则,不能逾越的界线。
选择凝视此刻的拥有
还是说回这趟行程吧。其中一位负责接待的,是名叫恰克拉(Chakra)的中年男子。如同许多释迦族的后裔,他也是一位铜雕师。忘了是行程中的第几天,早餐在酒店餐馆遇见我时,他给我送了一枚银坠,是一张观音菩萨的脸相。“是我自己雕的。”他说,语气里不无自豪。
然后他递来一串念珠,“这是金刚菩提,是我们尼泊尔的特产。”我于是伸出右手,他慎重地为我戴上。
金刚菩提,状似核桃,网路上盛传那是佛陀成道时结跏趺坐的菩提树的果核,但我认为不是。常见金刚菩提有红褐二色,呈多瓣状,一般多为五瓣。
《佛说校量数珠功德经》里记载着,不同材质的念珠,其功德各异,如铁,如赤铜,如珍珠、珊瑚、木槵子、莲子、水晶……,其中以菩提子为最,“数诵一遍其福无量,不可算数难可校量”。然而S’s,你知道我向来对这些形式化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从不认真看待,但不知怎的,我还真喜欢那串金刚菩提,于是整个行程都一直穿戴着。
对于恰克拉,我一直深感愧疚,不是因为接受了他的礼物,而是因着我的小人之心。
话说有那么一天在帕坦,他带着我和部份团员到一间名叫Rudra Varna Mahavihar的寺庙。那原就不在行程里,抵达时才发现原来需购买门票。亲爱的S’s,你知道我在旅游业里的那几年一直很不愉快,我反射性地以为又是业者惯见的恶劣技俩,心里甚不舒畅。团员们倒是没我小心眼,问说门票怎么算,他憨厚地摇着手,努力思索着词汇,然后说:“不用、不用……”
庙很小,恰克拉还在忙着与撕票员点算人数,团员们就径自转了一圈,从出口处走了出去。恰克拉回过神时,就只看见我一人了。我向来敏感,那一刹那,我看见了他的愕然。
恰克拉费力地用中文单字与不流利的英语告诉我,他参与了这寺庙的修复工作,壁上的铜雕,正是他的手艺。我恍然明白,他如斯渴望我们到寺庙来,甚至不惜自掏腰包给我们买门票,是因为想与我们分享他的喜悦——释迦族向来都以自身的手艺为荣。
我们的匆匆,显然辜负了他的心意,甚至未及细看他的努力。我感受着他的感受,不禁自己失落了起来。而且,我竟还一度以着小人之心……
我后来才知,原来Rudra Varna Mahavihar是帕坦有名的古寺,拥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当然,那是我回来以后才知的事情。
S’s,这篇文章的书写,缘于思念。然而思念,思念,终将消弭殆尽,或以着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我知道。于是我选择凝视,凝视此刻的拥有,遂心满意足。
我说了,这趟行程我带上了《流浪者之歌》,果不其然,并未读完。夜里,酒后,我放下了书本,走出了旅店。
夜凉,如水,街上行人不断,但或许因为城里没有霓虹灯,依然很是安静。有个年轻男子向我走来,“要大麻吗,大麻。”他殷切地问。我笑着摇摇头。他以为我是中国旅客,努力用有限的中文词汇与我攀谈。我于是知悉他白天在中国商行里工作,夜里则出来兼职,兜售大麻。为了生活,他说,生活。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Lucky。”然后他补充:“我有许多名字。在这里,我是lucky;在其它地方,我有不同的名字;白天,我是另一个名字。”
S’s,或许你会觉得难以置信,但在那一瞬间,我在他脸上捕捉到了苍凉。是的,苍凉,不属于年轻人该有的苍凉。因为生活。
于是我知道,我终将再来,以着行人的姿态,单独前来,为着更认识这座城市的人与事,为着前往佛陀的出生地蓝毗尼,为着加德满都七大世界遗产中的帕斯帕提那神庙。
帕斯帕提那,供奉的主神是婆罗门的湿婆神。湿婆神,毁灭之神,同时也是汉传佛教家喻户晓的《大悲咒》里所赞颂的青颈观音。
庙旁,有一条巴格马蒂河,流向印度恒河。河旁常有露天的火葬仪式;庙里有许多苦行僧,是境内唯一可以合法吸食大麻的地方。于是流浪汉、瘾君子也混入其中,龙蛇混杂。这样的地方,断然是必须单独前往的。
于是,我终将再来。彼时,思念不再,碎语不复;因为,我终究只是你生命里的一个旅人。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