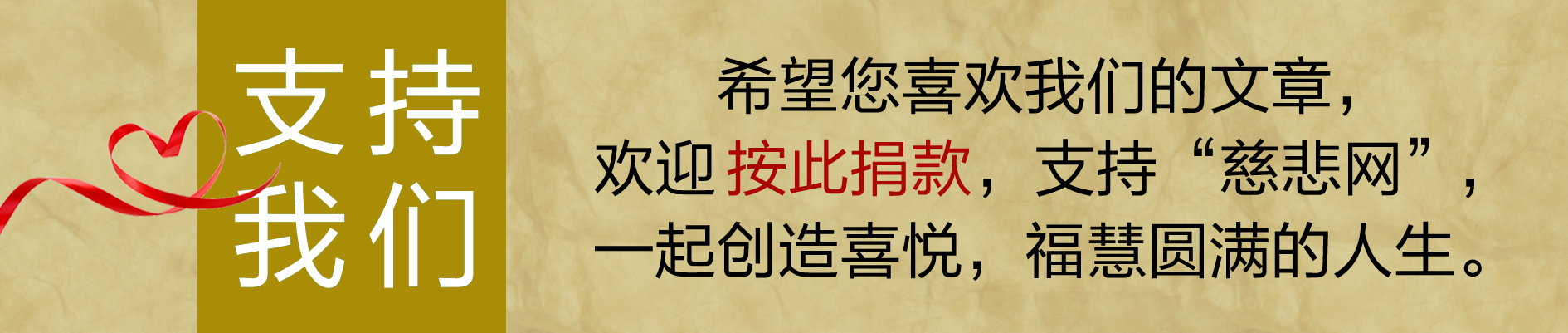阿根廷南极圈内的莫连奴冰川,那么遥远,但它越来越频密的崩溃惨叫,身在北半球的人类多数都充耳不闻。
·
少年的沉默?
这般屹立着毫不动摇的冷静,
就是一股愤然不顾,
自己守住属于自己的疆界。
·

原来真有那么古老的冰雪?千万年没有融化,以致水份里的化学物使它逐渐累积成一层层不同的蓝色。
要向那心情冷静的冰雪好好学习
当我第一眼看到浮在安静兀沙拉冰湖上的巨大蓝色冰雪,心里像被重重撞击了一下,很震惊的。
原来真有那么古老的冰雪?千万年没有融化,以致水份里的化学物使它逐渐累积成一层层不同的蓝色。
我眼前这下子就显得特别安静,兀沙拉冰湖附近已经属于极圈无风带,水面上只是我们船只驶过的微微波纹,四周安静得就像藏着什么秘密,盛夏的极圈天色微微发紫,这不是一般世界的风景,倒似一处只允许瞬间闪现的秘境。我们的船也停下了马达,仿佛生怕再靠近些,就会打扰它们。
南极圈,有点阴冷,但我是刻意就一个人去的。好好去冷一下静一下。
这些浮在冰湖上的巨型冰块,照片上看只属巨型,但实际上很多都有二十多层楼的高度,一艘在我们前面远处经过冰块的船只,就像粒小米一样。
多少年的沉默?这般屹立着毫不动摇的冷静,就是一股愤然不顾,自己守住属于自己的疆界。

冰湖附近已经属于极圈无风带,水面上只是我们船只驶过的微微波纹,四周安静得就像藏着什么秘密。
有些浮动的冰山会相遇一起,然后再组合成更大片的冰山群,像在冰湖上排练着一出玲珑剔透的塑像舞台剧。
船员捞上一块浮到船身的冰块,是,浅蓝色的,他将它放在船舱吧台上给人观赏,这块千万年的一片小小部分,虽在寒冷的空气里也会慢慢融化,谁都留不住我。
甲板上都是啧啧称奇的人们。为什么这些小冰山能浮在原处一动不动?为什么这为什么那,洋人喜欢探讨,但我只想多点感觉它们。
一路远道而来,从人间地狱般的巴西里约热内卢来到犹如世外的阿根廷卡拉法德,森罗世界光怪陆离,还真是炎凉尝尽,一下子面对这些执着于屹立的冷峻脾气,我像明白了一些什么,要学会拒绝,要学会抽身隔离,从此更要学会说不。

盛夏的极圈天色微微发紫,这不是一般世界的风景,倒似一处只允许瞬间闪现的秘境。
谁是这双雕塑的能手?冰山们形态神情各异,曲线处如大理石,崩裂处像一个冷冷的火山刚爆发过。冰山们各自映照着自己,对众人的惊讶无动于衷。真的,沉着,就是一种力量。
遍地衰草与残留的冰
很肯定,与冰山的邂逅,就这样深深影响了我。
其实才不过是两周前,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南下的内陆机还是老旧的737,摇摇晃晃抵达卡拉法德,这城镇不大,但宿舍其实离机场还很远。公车转入国道高速还飞驰了两小时,才抵达在石头湖畔的宿舍。
虽说夏天,白天气温最高就那么12度。午后气温骤然下降,冷了,是那种天地一声不响没头没脑就压下来的冷,而天色还算是亮的,不明朗,一种你知道只是剩下来的弱光。

在寺庙前餐风露宿就靠善有些浮动的冰山会相遇一起,然后再组合成更大片的冰山群,像在冰湖上排练着一出玲珑剔透的塑像舞台剧。信施舍度日的苦行者。

有些浮动的冰山会相遇一起,然后再组合成更大片的冰山群,像在冰湖上排练着一出玲珑剔透的塑像舞台剧。
宿舍虽简单,设备倒算齐全。但要命是宿舍的浴室竟然是露天的,那就只能一直开着热水往身上冲。隔壁一位德国大叔倒是聪明,拿着一瓶红酒边冲边喝。
卡拉法德最可爱之处就是自然而不造作。浴室后面原来就是融冰流下来的小山溪,溪旁全是松树与杉树,夏天它们就拼命吸取阳光,宿舍管理员说这里一到五月就开始天昏地暗,宿舍在五月中旬就得停业,到十月中旬才能重新开始。
小溪的水,其实到了中午阳光较强时并不会太冷,溪涧之中有许多石头,啊想起这里就靠近石头湖,问问管理员可否远足,他摇摇头,说,全球气温暖了那里现在危险,不如远足到多雷雪山的冰河去。


第二天宿舍就为我准备好远足申请和简单的食物,我自己带了些巧克力也就出发。多雷雪山第一个征服者是法国人,我没想爬上去,只想远远地走一段路,探望一下半山上的冰川。
忘了说这里也就是地球上最长山脉安第斯山的一支余脉,安第斯山,以恶地形著名,不过沿途偶尔会有人留下指示牌或一些记号,也并不太难。通往多雷雪山的路土壤比较潮湿,一路上还能见到草色,但仿佛营养不太好,遍地的衰草在一些夹着残冰的泥土里长出来,恶地形恶环境,我佩服那份生命力。倒是苔藓类,它们薄薄披在沿途潮湿的石头上,不仅长得好,甚至还能开出极微小极微小的花。我第一次看到苔藓类的花,万籁俱静中惊讶良久,真的,有时候越是低微,就越能适应一切。

陪着情人的多雷雪山
探访多雷雪山,单程就要付出约五个半小时的远足代价,黎明出发,下午一点才真正爬上冰川所在地。要临近之前,还发现多雷雪山极有心思,曲曲折折的小径让人感觉前方已是疑无路,怎料一个拐弯,原来雪山就在眼前闪烁映亮地微笑。
多雷雪山活脱脱就是一个象形的山字。三个主峰雄伟陡峭,山色层次极为分明,是一座很英俊的山脉,它把自己身影映照在面前冰川融化的大湖上,大概也知道自己长得帅气,像躲在地球的末端静静地自己照着镜子。
雪山下的冰川,看似靠近,其实从望到它之后要走到冰川那还得步行七八公里。雪山与冰川,在这人烟少至的南极圈内就像一对远离尘嚣的恋人,深情款款地互相陪伴着对方。我发现在周围前来远足的也就只有几个人,我们都是远远地望着雪山,大家也不认识,但大家都在雪山之前躺坐下来了,一起陪陪这对美丽的恋人。

听说也有人在这里扎营过夜的,因为一到夜里这里的天空澄明得能够以肉眼望到天上的银河,我实在后悔没有申请扎营过夜的准证。不过我在心里说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再回来这里。后来在回程上,水完了,路还长,但我还是这么觉得,我日后一定要再回来。
臭氧层破裂造成多处大树坟场
休息一天做足准备功课,我还是偷偷地越过宿舍后面小溪,去找石头湖了。
因为有些事情不明白,就感觉这里景观很特别。原以为靠近湖泊那么一路上会是茂密树林,但事实上这里犹如砂石半沙漠,漫山遍野都是荆棘及一些很耐旱的植被。这里偶尔也会看到树,但却是一处一堆地而不是一整片地生长,正在狐疑之间,就被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景观——我没想到一个转身,眼前就是一大片灰白色枯死的树干,那情景就像昨晚有UFO飞过向地上作了一次镭射毁灭。后来回到宿舍才知道,原来这一带受到臭氧层破裂的毁灭性照射,是强烈紫外线烧死了这些大树,它们死去的树干虽然还站立着但其实只要轻轻一碰就会轰然倒下,因为它们其实早已经烧成了灰,只因为少雨无风才因此一棵棵还站立着。这些有大树坟场的地方也已部分封锁,难怪宿舍人员不建议我到此远足。

倒是苔藓类,薄薄披在潮湿石头上不仅长得好,甚至还能开出极微小极微小的花。当它们整片时就如大地上的艳丽刺绣,万籁俱静中教人惊讶良久。
不过,再多灾苦难的地方,也仍会有能够适应的坚强生命力。在一些岩石的缝隙地下或是阴影之下,常常能看到一种从没见过的美丽小花;像是兰科又像是洋水仙,娇小玲珑的鲜黄色,在这片恶地形上尤为触目,而我,每次遇上了它们,很奇怪,我就觉得这路是对的,这路还安全。
宿舍里人不多,算来算去也就那十来位住客,而愿意来到这里的人,也大都属于喜欢清静的一群,晚饭后在大厅上各做各事,有时真的连放下一只茶杯都成为很刺耳的声响。不过还好,大家在厨房一齐做饭,碰面多了也就成为朋友。几位德国人约我一齐去看莫连奴冰川,说还欠一人方能成行,我答应了。
人类垃圾最终会毁了自己
莫连奴冰川公园距离宿舍并不远,大约30公里路程。冰川国家公园里必须有他们自己的响导,不允许私自乱闯。

还没看到世界著名的莫连奴冰川就被公园里一个景象吓到傻了,我看到走在前面的德国人后颈上黑麻麻的堆了一堆东西,跟他说了声他就用手去扫,天啊原来是难以想像的巨型蚊子。
这些巨型蚊子足有小蜻蜓般的大小,而且像轰炸机那样追人。
响导其实也就是南极圈生态研究员,他说因为臭氧层破裂,部分生态受到辐射而发生剧变,这只是其中一例。
莫连奴冰川最终抵达了。足有20公里那么宽阔的冰川,就平躺在阿根廷湖泊的西面,没看清楚的话还以为是一片宽阔的雪原。
巨大到摄人神魂。冰川底层之下的雪是浅蓝色及白色的,但冰川上面,却像是又黑又脏的黑泥一般。
响导说那不是泥,那都是人类的垃圾。北半球的二氧化碳与排放出来的尘埃最终都会漂流到南极圈这个尽头,累积久了,许多原本洁净的冰川与雪山,都蒙上这么一层垃圾。

话说未完就听到眼前的冰川轰然一声巨响,冰川崩溃了一大片,从高处跌下冰湖里溅起了巨大水花。一些在不远处的洋人欢呼大叫,个个拍下伟大镜头。
响导语气听似平淡,其实,我相信那已是一种麻木,他说:请不要欢呼这个崩溃。冰川在90年代初期的气候里是每8个月才出现一次崩溃,现在,每40分钟你就能听到人们不知死活的欢呼了。
全球暖化,工业排放,文明开发,统统都给大自然制造数不完的垃圾,莫连奴冰川终会有天也随着消失殆尽。
人类垃圾最终只会害死自己。
但多少人能听的进去呢?莫连奴冰川那么遥远,它越来越频密的崩溃惨叫,身在北半球的人类多数都充耳不闻。不过,对我来说,南极圈一行,无疑就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一课;它的遥远,它的执着,它的咆哮,也是让我深思至今的一课。


1951年出生,新加坡作家,早年于英国进修美术设计,自80年代初期背包环球旅行后开始专业写作,着有小说、散文、游记等23册。其游记《背包走天涯》全套5集系列曾启动80年代本地年轻人背包闯荡世界的风潮。
評論